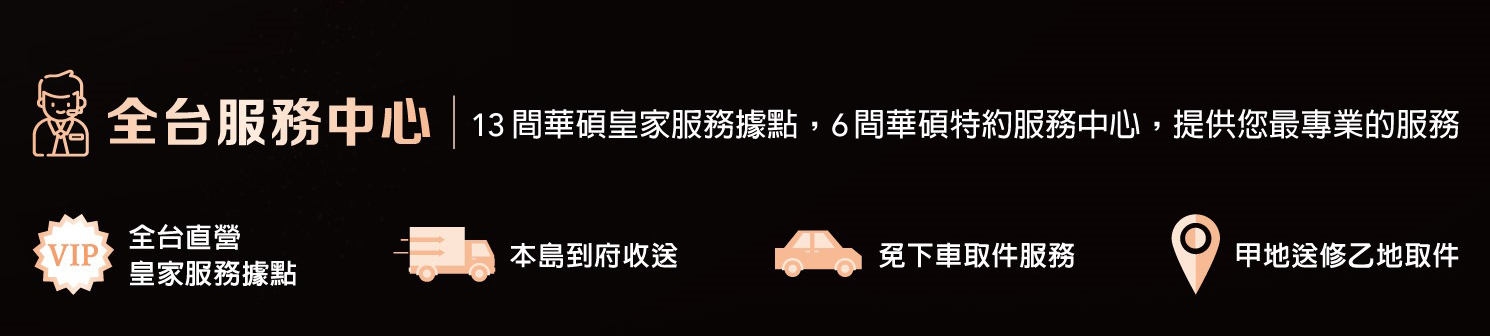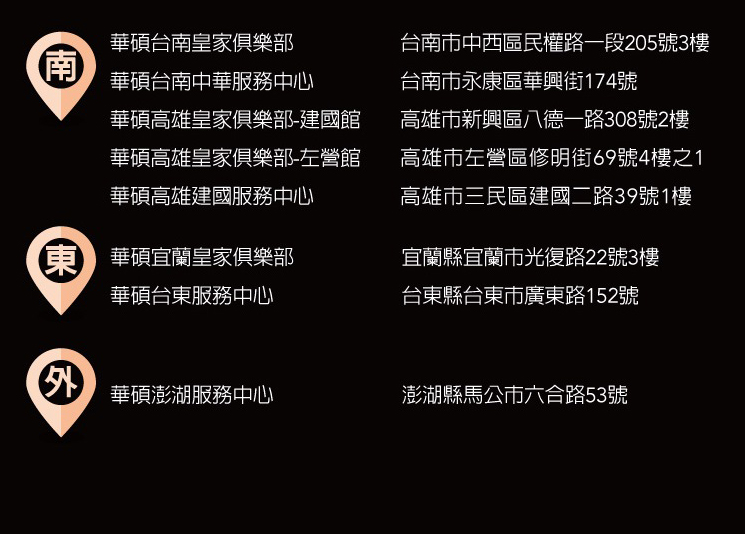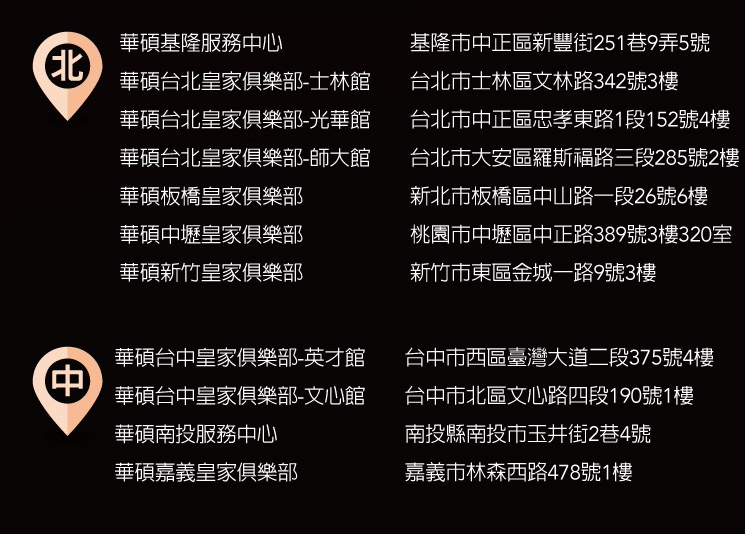如何抵達人心,如何為愛畫刻度:駱以軍的文學啟蒙小說26講
ISBN13:9786263106383
出版社:麥田
作者:駱以軍
出版日:2024/03/31
裝訂/頁數:平裝/288頁
規格:21cm*14.8cm*2.2cm (高/寬/厚)
版次:1
定 價:NT$450 元
【內容】
駱以軍召回年少時文學啟蒙時光,
面對生存的惘惘威脅,如何經歷讀小說「最初的撼動」!
透過26篇經典深談與讀者共情,
鋪展人心與愛、與世界的燦亮連結。
◎ 收錄作者介紹引領其進入小說世界,並影響、滋養其創作能量的重要經典作品,以感性與知性兼具、非嚴肅評論的散文分享,與讀者交心,一窺經典小說堂奧。
◎ 米蘭昆德拉/杜斯妥也夫斯基/莒哈絲/馬奎斯/川端康成/三島由紀夫/夏目漱石/太宰治/張愛玲/沈從文/王安憶/李渝/白先勇/王文興/舞鶴/童偉格⋯⋯匯聚各國經典分享,精萃當代文青必讀文學圖像。匯聚各國經典分享,精萃當代文青必讀文學圖像。
跟著《麥田捕手》的青年一路流浪擦傷,
堅定直面眼前陰翳昏閃的偽善世界;
或循著三島由紀夫的魔幻之筆,
拾級登上絕美金閣寺,如何燒灼、折磨並凌遲自己的心志,
內心狂潮翻湧的瞬間,卻將眼前希望付之一炬⋯⋯
駱以軍的青年時光,圍繞著經典小說家擘畫出另一個心靈宇宙,
將晦曖俗世的殘缺卑瑣,連同世間對各種希冀的盼望追求,
交融成一場「美的核爆」,引領他如何共情、如何旁觀他人之痛苦,
璀亮煙花就這麼墜落在少年的文學凝視之間,
至今未曾停歇。
「這本書的起心動念,是想像面對一室對小說有憧憬的年輕人,類乎散談,促膝交心,回憶我自己二十出頭時,懵懵懂懂,與世界像隔著煤污車窗玻璃,在毫無足夠經驗與教養的狀態,第一次讀到川端,第一次讀到夏目潄石,第一次讀到馬奎斯,第一次讀到杜斯妥也夫斯基,第一次讀到福克納,第一次讀到張愛玲……都只是他們小說中的其中一本,或一章節,對那時的我的內心,像是『世界被另一種次元,全部核爆、重置、拗扭成另一種物理概念』,像一顆原本空寂、貧乏的火星表面,突然被這些小說神人,帶來的漫天雷擊、大雨滂沱、烈焰滴淌、不可思議的極光,或之前完全沒有夢見過的森林繁複植株、禽鳥、獵食生物鏈、生滅的演劇……」——駱以軍
本書收錄作家駱以軍青少年時期重要的閱讀滋養,二十六篇散文並非嚴肅的文學分析,而是意興遄飛、如蚌貝吐沙般召回被經典觸動的美好記憶。時間回溯到作者八○年代,仍深陷台北街頭小混混、青少年鬥歐的狂躁青春,鎮日被教官廣播至訓導處報到。這樣一個青少年,如何像阿里巴巴打開藏寶洞般,在各個作家與經典中旋身,透過獨自於陽明山學生宿舍日復一日的文學抄讀,進而深受啟蒙,不斷被小說震懾、附魔,自此改變其眼瞳向外觀看、向內反芻自省的方式;在小說之眼的窺探下,打開對世界與自我內裡的深層連結,於各種黑白畫片折射出令人驚異的輝芒。
透過這本書的分享,作者欲建立嚮往文學的讀者與經典之間,一條驚喜不斷的廊道。自駱以軍的閱讀記憶,揭開小說背後的大歷史,分享二十世紀文明經歷了什麼超乎個人的重大噩夢,關於張愛玲、杜斯妥也夫斯基、川端或三島、沈從文、年輕狼狽的馬奎斯、在銀行安靜上班的卡夫卡,他們各自在各自「惘惘的威脅」,在那眼瞳之玻璃窗外或內,折射了什麼怪異、不可思議、瑰麗或恐怖的風景?
【內文摘錄】
「昆德拉寫到『同情』──並不是我們最初對這個詞的固見:可憐、不忍悲憫──不是的,而是,因為妳是我深愛的那個人,所以妳內心全部的感覺,妳的痛苦、妳的童年創傷、妳對我的不忠所感到的錐心,或是妳對置身這個世界的那種一不小心就碎裂的『惘惘的威脅』,我全部能感受。同等程度的痛感。這其實該說是『共情』。」——〈他感〉
「我年輕時幾度當作攻堅,打開普魯斯特的《追憶逝水年華》,然皆無法進入,讀著讀著便昏昏欲睡。實則是內在做處理,運算的『硬碟』容量太小了,無法同時吞納那麼龐大、不斷漫漶的細節。對《紅樓夢》的體會亦如此,年紀愈增,每隔幾年,再次重讀,那個『疊加』而上的,年輕時略過的影綽,以為是無關緊要的側筆、暗筆,這時湧上的那個『靈光乍現』,擊節佩歎,才知偉大小說的無窮妙處。」——〈那個極限的光〉
「仔細回首,杜氏小說中的人物之罪,之惡,比起後來這一百多年來,人類所犯下無論從其規模、怪誕、驚悚──不管是納粹集中營創造出來的無邊地獄,或史達林的大清洗乃至種族滅絕,或文革的在中國城市或農村,後來這許多小說家寫之不盡的『純粹的惡,純粹的集體瘋狂』,或是無論大江、納博可夫,或是韋勒貝克,其實他們『眼瞳被灼燒變成灰白』所見的惡的繁複、怪異、內凹變形,甚至不用小說家!」——〈惡之謎團〉
「『笑』必然有一社會性的截裁、時代共有經驗的有效性。另外就是『語言的本身』。你如何對自己與身邊人共同的這套語言,它的靈活或破綻,心領神會,它其實和抒情詩與流行情歌的關係一樣,如要殺雞取卵,快速兌現,就愈難成為『經得起時光淘汰』的結晶。」——
〈「笑」的感受力〉
「我可以做出這樣或有人覺得裝神弄鬼,但我真摯沒有懷疑過的『小說家的道德』:每一次都是他『另一次的死亡』。我年輕時有一執拗的迷信(因為真的很巧,每次都發生了),我每寫出一本對我極重要的小說,上天就會奪走一件,我最珍愛的東西:我最愛的那隻狗、我父親的生命、當時我妻子對我的愛,我極在乎、愛著的一位長輩莫名的仇恨我、我的健康,乃至我的聲名……在不同時期它們真實都發生了。」——〈另一個心靈宇宙〉